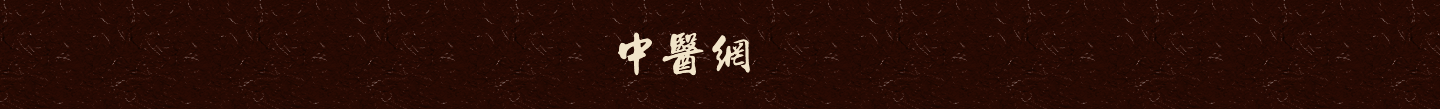杨克当代民族文学的内置型边地书写
中医丰胸 2020年07月10日 浏览:3 次
邱婧 (邱婧,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新时期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流变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5CZW058)
在讨论少数民族文学定义及其界定的时候,通常会围绕着两重标准展开:文学写作者是否具有民族身份,以及写作的题材和内容是否反映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或日常生活。在民族文学研究者李鸿然看来,这一概念和界定可以追溯到茅盾那里 早在1949年,茅盾在《人民文学》的发刊词中就提出 少数民族文学 的概念,并且认为作家应具有民族身份,以及作品应具有民族特点[①]
。毫无疑问,学界将同时具备这两种条件的作家文学称之为少数民族文学。除此之外,关于这两重标准还有一些争议,其争议的焦点正在于两方面:少数民族写作的非民族题材的作品、汉族作家写作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是否可以纳入到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
于是,在数十年的学界探讨中,似乎形成了一个惯例,如果创作者的身份是少数民族,并且他创作的文学并不具有少数民族精神气质和生活特征,也可以纳入少数民族文学的范围;然而,汉族创作者即便在作品中体现了少数民族特色和民族传统,也不会被称为少数民族文学。在我看来,这恰恰指向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边界。杨克的早期诗歌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作为广西汉族诗人的杨克,提出的 百越境界 说曾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界探讨的热点,其关于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的诗歌书写不仅指向了广泛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并且以其汉族身份、少数民族素材成为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例证,其关于边地文明的 内置型 文化身份的书写也是十分值得探讨的议题之一。
一 从 寻根文学 谈起
上世纪80年代的广西文坛异彩纷呈,1985年的《广西文学》上,先后发表了杨克的《走向花山》组诗以及杨克、梅帅元《百越境界 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一文。位于广西的壮族花山文化有着神秘而悠久的历史底蕴,其中花山崖壁画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包括左江流域壮族聚居区的凭祥、龙洲、宁明、崇左、扶绥、大新等地。同年,杨克又发表了《红河的图腾》一诗,亦是根植于广西大地丰饶的民族文化而作。值得注意的是,杨克这一系列的文学表述被批评界列入了 寻根文学 的队列,当代文学界的很多学者将杨克的诗歌创作归纳为对传统文化的追寻,而广西文学在这一时期也被当作寻根文学的重要而隐匿的阵地之一[②]
。
事实上,杨克早期诗歌《走向花山》和红水河系列简单地归为 追寻传统 并不贴切,这需要返回历史现场,从关于寻根文学的学理论证说起。姚新勇曾提出一个从文化多元视角出发的看法: 泛寻根文学思潮 [③]
,他认为,在狭义的文学史限定的 寻根文学 出现之前,需要注意到广谱的
文化寻根 ,而这个发生在广袤的土地上的寻根牵涉到了汉族作家和少数民族作家的广泛参与,比如彝族的诗人吉狄马加、藏族的作家扎西达娃,回族作家张承志等等,并且这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引起了国际文学界的着力关注。
在这样的话语场内,杨克的诗歌书写独树一帜,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界性。他的 花山 和 红水河 写作无法简单定义为追寻传统,如果从诗歌文本出发,则能更好的证明这一点。在他的《走向花山》中,如是写道:
欧唷唷 /我是血的礼赞,我是火的膜拜/从野猪凶狠的獠牙上来/从雉鸡发抖的羽翎中来/从神秘的图腾和饰佩的兽骨上来/我扑灭了饿狼眼中饕餮的绿火/我震慑了猛虎额门斑斓的光焰/追逐利箭的铮鏦而来 /践踏毙兽的抽搐而来/血哟,火哟/狞厉的美哟/我们举剑而来,击鼓而来,鸣金而来/ 尼罗!从小米醉人的穗子上来/从苞谷灿烂的缨子中来/从山垌场和斗笠就能盖住的田坝上来/我是血之礼赞,我是火之膜拜/抡着砍刀的呼啸而来/仗着烧荒的烈焰而来/血哟,火哟/丰腴的美哟/我们唱欢而来,雀跃而来,舞蹈而来/ 尼罗! [④]
这首诗歌的创作背景是基于杨克对花山崖壁画的考察,此岩画位于广西宁明,是大批壮族先民骆越人绘制的赭红色岩画,一说是祭祀留下的遗迹,距今已经两千多年,是较为壮观的文化遗产。如果避而不谈诗人杨克的族裔身份,那么读者应该倾向于这是一首少数民族诗歌。且不提 血 与 火 的礼赞,仅在节选部分的最后一句 我们唱欢而来 ,就可以彰显诗歌的民族性。诗人特意在诗歌后附了注释: 欢 是壮歌的意思,因此显示了这是一首关于壮族文化的诗歌。他几乎是在书写民族志一般的诗歌。 野猪 、 雉鸡 、 猛虎 、 利箭 这样的词汇,仿佛在展示一个人类学图景:刀耕火种,祭祀神灵。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诗歌创作的时间节点 1985年,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族性写作还处在萌芽阶段,尚未呈星火燎原之态,而以汉族代言人身份写少数民族题材的诗歌范式又已经慢慢消失。杨克在这一民族文学的转型期写出如此高质量的诗歌作品,是十分值得注意的,而将其简单地视为 追寻传统 又是不恰当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传统的释义是 从历史上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尚、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 。而在杨克的写作中,我们需要追问,如果说这是一场文化寻根,那么,追寻的是 谁的传统 ?此问题将杨克的早期诗学置入了杂糅而多元的文化场域,那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边界,亦是内置性的 边地书写 。
二 内置型 边地书写的发轫
在我看来,当代诗歌的边地书写可以分为两种, 外来型 的和 内置型 的。前者是作为外来闯入者对少数民族或边疆风景的表述,而杨克的诗歌显然属于后者,他生长在广西,生长在百越文化之中,其早期诗歌离不开百越文化传统的滋养。如何就这两个类型进行区分和界定,也是下文需要分析的焦点。
当代汉语文学的边地书写与边疆想象,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诗人公刘及其作品。公刘早年参加学生运动,后加入解放军,广州解放后,他随军进入大西南,随后书写了一大批的关于民族题材的诗歌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54年出版的《边地短歌》。比如,公刘曾在《哀牢彝歌》中如是写道: 圣人出在北京城/圣人就是毛泽东/他带领几百万红汉人/上山来搭救我们彝人/手抹桌子一般平/彝人汉人骨肉亲/人人都听毛主席的话/建设各民族的大家庭/这一片土地/山是我们的山/河是我们的河/就是一粒沙、一滴水/都只能属于中国!/这是个美丽的地方/它丰富,但曾经贫困/它美妙,但曾经荒凉/拿喜人披了几千年的羊皮/西藏人赶了几千年的马帮....../这就是美丽的丽江/这就是魅人的丽江/等待着开昼的处女地哟/能带给它春天的,只有共产党! [⑤]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位江西南昌的汉族诗人,公刘来到中国的西南边疆,对民族风情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抒情感怀,这样的表述显然是 外来型 的,而出生于广西的杨克则不然,他的《走向花山》和红水河系列的诗歌彰显了民族文学的 内置型 。杨克作为当时书写民族题材的青年诗人,他曾这样回忆自己参加南宁诗会时的情景: 我作为学生,不仅负责会议全过程的录音,公刘先生谈顾城诗歌的发言也是我给他整理的。 [⑥]
然而,杨克却改变了自公刘以来的边地书写的诗歌话语形态,从外来者的眼光变成了内置的、在地性的书写。
值得注意的是,杨克的 内置型 边地书写的发生绝非偶然。1955年,壮族作家韦其麟的《百鸟衣》出版,是中国当代民间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另外,与此同时,鉴于部分少数民族还不曾熟练掌握汉语,汉族的文艺工作者的边疆书写也呈现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界性,为少数民族代言的诗歌不断涌现。197 年出版的《红水河欢歌》[⑦]
便是一个例证。时过境迁,十余年后,汉族诗人梅帅元、杨克撰写的《百越境界 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一文[⑧]中,首次发出 百越境界
的呼声,又一次指向了 花山 、
红水河 等地理空间和文化意象,并且引起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的重视
[⑨]
,亦使得广西文坛的实力呈现在全国文艺界的视野中。
上文提到,杨克的组诗《走向花山》想象再现了壮族先民的生活图景。他选取自己在文化考察中发现的花山崖壁画中的典型图案,植入到诗歌之中;而在他的《红河的图腾》组诗中,则展现了广西红水河文化的厚重历史图景。其中《深谷流火》这一首写到: 红水河/是从石头里走/出/来/的/大朵大朵的木棉花/温和地焚烧着/山很粗糙/铜质阳光/凝滞在峡谷里/玄色鸟/血浪/巉岩般一动不动的山民/ 的脊背/泛动与土地天空浑然的赭红/(山羊咩咩的叫声也是红色的么?)/狞野的神话旷达的神话洒脱的神话/愈流愈远上游漂下来喧闹的日子/陌生的日子新鲜的日子不安的日子/匆匆地漂下来漂/下/ 来/雄性的风/呼啸着令人嫉妒的 /这水是点得燃的哦/一团团火球/醉醺醺/醉醺醺/ 旋转/红水河/大山的血脉/烈焰汹涌的血脉哦 [⑩]
红水河流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域,诗人在这首诗中挖掘地方性知识,着意用粗粝的笔触勾勒红水河文化的神话传统与历史变迁。事实上,这样的写法在很多少数民族诗人笔下是频繁出现的,他们往往善于用巨大的历史画卷来彰显 想象的共同体 , 安东尼 史密斯曾经就这个现象做出评价: 英雄们的开拓奋进、各路先贤和传奇故事都在这块土地上发生 有哪种民族主义会不对为各路神灵所保佑的, 我们自己的 山川河流、湖泊平原的独特壮美称颂备至? [11]
然而,在汉族诗人的笔下则很少出现宏大的史诗意象,杨克的诗作很值得注意。
不仅如此,他还在另外一首诗中体现了 迁徙 这样的民族志意象。在《大迁移》中,他写道: 举 过 头 顶/将芬芳的酒坛举过头顶/将封闭的岁月举过头顶/颤抖的手/山毛榉似的随着粗重的呼吸摇曳/酒的瀑布/倾/泻/神秘的棕红色的火舌/突然蓝得叫人窒息/火塘,腾起一股孤烟/古朴宁静的陶土罐破碎了/告别是白色的/哗然而下的纸幡/从山头/泻入/谷底/起伏如波浪/全寨子无声的目光沉重的目光/无声的沉重的全寨子目光/缓缓漂移/悬崖一样沉默墓碑/像孤零零的岛屿/山鬼与水妖成亲的传说成为可能
尽管在诗人的注释中,可以得知这是一场因建设水电站而导致的现代迁移,然而宏大的仪式性依然令人震撼不已。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很多南方民族都有着迁徙的历史和口传史诗,杨克恰恰把这种迁徙的传统完整地内化为边地书写,时间性在诗歌中不断呈现。另外, 酒坛 、 火塘 、 寨子 这样的意象时刻在提醒读者,这不是闯入者的 代言 ,而是真实地体现了少数民族面对现代性的阵痛与伤感。因此在这首诗中,更加凸显了杨克早期诗歌的内置型民族文学书写。与其说是人文关怀,毋宁说是发自内心的悲歌,这种全球化和现代性对当地文化的冲击,与组诗中的其他章节构成了延续和对应关系。
三 多元与共生的文化场域
广西地处亚热带,原始文化与楚文化的融合,形成百越民族特有的审美意识,创造了本地域灿烂的文化。非常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广西作者只把注意力放在以京、津、沪作家为代表的流行的文学观念上,使得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成了别人的重复。 [12]
这是梅帅元、杨克在《百越境界 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中所提出的看法。
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构建中,这段话尤其值得注意。正如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杨克所生长生活的广西百越文化滋养了广西的作家群,这并不是某一个民族专属的,而更像是某种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壮族学者梁庭望在分析中华文化板块结构的时候,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将中国文化板块分为四大板块,十一个文化区,并将广西文化置于江南稻作文化圈,华南文化区[1 ]
。这又牵涉到本文第一节提出的问题:杨克的 追寻传统
是谁的传统?
尽管花山文化和红水河文化都是广西壮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然而按照梁庭望的考察,壮族的文学谱系 演绎是:一团急速旋转的气体 三黄神蛋 三层宇宙 姆六甲 布罗陀 布伯 伏羲兄妹 磨刀石形肉团 新人类 , 汉族的人文祖先伏羲女娲进入了壮族的神话系统 [14]
,另外,他提到在当代广西民间文学中,《刘三姐》的壮族民歌歌词也是由壮族、汉族、仡佬族等多民族作家共同完成[15]。广西是多元文化共生的一个重要场域,而杨克的写作恰恰生长在这一文学场域中,因此将 寻根
细化,便是多元共生的多民族文学传统,这正是杨克被当代文坛所忽视的重要写作特征之一。
继续内化广西的多民族文学传统,可以用汪晖的跨体系社会来解释。汪晖认为,跨体系社会是 经由文化传播、交往、融合及并存而产生的一个社会,即一个内含着复杂体系的社会 [16]
,基于这个理论,汪荣提出 跨民族连带
的关键词,他认为尽管各民族之间的 生活习俗、精神信仰、文化记忆不同,但是在历史发展与地缘交汇中,他们彼此共生、彼此缠绕
少数民族文学则是表征这种连带的最佳载体 [17],这并不局限于少数民族文学,广西文坛正是一个 跨民族连带
的经典范例,除了杨克以外,当时还有一大批汉族及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投入到 百越境界
的讨论和创作实践中,构成了广西文坛的丰饶景象。究其原因,以汉族和少数民族为主体共同构建的多民族汉语文学,其语言具有混血性和杂糅性,铸就了优秀的文学作品。
正如杨克在《大迁移》的末尾写的那样: 擂响铜鼓擂响大山擂响太阳/蹲葬和断发文身的历史/永远永远遗弃在崖壁上永远永远/布洛陀的后裔/沿着红河的走向/山脉的走向/悲/歌/行/进 [18]
。断发文身,是壮族早期的审美范式;而《布洛陀》亦是壮族的传统史诗,在诗人的笔下,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性显现出来,我曾经多次在很多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看到这样的切肤之痛,这又一次证明杨克的早期诗作可以被当作讨论民族文学边界性的经典案例。
值得一提是,在发表花山组诗和红水河系列组诗的同年,杨克还曾在《民族文学研究》上撰文探讨民族学与美学的关系,他认为 著名的花山崖壁画,既描绘了壮族先民的生产生活图景,又反映了壮族先民的宗教和审美观念。 [19]
除此之外,文中他对广西的多民族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举证,足以证明其写作的在地性以及其多元的文化身份。
尽管本文主要论述作为民族题材的杨克的早期诗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杨克去了广州,其诗歌书写有所转向,民间立场的城市书写成为其重要的创作特征,然而其早期诗歌对于广西文学乃至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构建都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因此, 内置 的边地写作恰恰是民族文学的临界点,例如当代诗人王小妮具有满族身份,但无论是诗歌批评界还是其本人,从来都不曾涉及到她的族裔身份,更未从她的诗歌中去挖掘关于民族性的论证,这正是研究多民族文学需要克服的边界性,也为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双重标准提供了有效的建议。
[①]
李鸿然:《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提出与确定》,载《民族文学研究》,1999年2月。
[②]
黎学锐:《八十年代中的广西青年诗歌》,载《南方文坛》,2008年6月。
[③]
姚新勇:《多义的文化寻根》,载《暨南学报》,2008年7月。
[④]
杨克:《走向花山》组诗,载《广西文学》,1985年第1期。
[⑤]
公刘:《边地短歌》,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1954年版,页。
[⑥]
杨克:《记忆:与 〈自行车〉有关的广西诗歌背景》,载 《南方文坛》 2001年第5期。
[⑦]
广西壮族自治区征文办公室:《红水河欢歌》,广西人民出版社,197 年版。
[⑧]
梅帅元,杨克:《百越境界 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载《广西文学》,1985年第 期。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还曾举行 百越境界 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讨论会。
[⑩]
杨克:《太阳鸟》,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11]
【英】安东尼 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8月版, 5页。
[12]
梅帅元,杨克:《百越境界 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载《广西文学》,1985年第 期。
[1 ]
梁庭望:《中华文化板块结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
[14]
梁庭望:《中华文化板块结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25页。
[15]
《阿诗玛》第二次整理本序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
[16]
汪晖:《中国:跨体系的社会》,《中华读书报》,2010年4月14日第52期第1 版。
[17]
汪荣:《跨民族连带:作为比较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载《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 期。
[18]
杨克:《太阳鸟》,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19]
杨克,黄伦生:《 民族与民族审美意识 试论民族学与美学的联系》,载《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1期。
六安白癜风中卫白癜病医院婴儿肚子胀气如何快速消除
- 上一篇: 灵界神座第一百三十二章血红玛琳
- 下一篇 肠胃不好可以吃苦瓜吗

-
中医中药中国行走进西双版纳
2019-07-15

-
鸡爪枝皮的功效与作用
2019-07-07

-
蓝花茶的功效与作用
2019-07-07

-
2019年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5月1
2019-07-05

-
可以美白护肤的食疗都有哪些
2019-07-05

-
毛连的功效与作用
2019-06-25